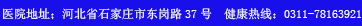小叙古意丨砚台
2023/9/21 来源:不详文|慧
人类文明自诞生时起,世人便竭尽所能,采取各种方式将文明的果实保留下来,使我们能够领略到先辈的风采与创造,同时也使我们的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文房用品,尤其是“文房四宝”,作为文明的载体起着重要的作用。
文房之名,起源于我国历史上南北朝时期(公元--年)。文房乃文人读书写字的房间,也是精神寄托的空间。文人可以在文房内独自焚香读书,也能给远方故友写诗寄情,或是和好友切磋琴艺,还能畅论古今针砭时弊,更有冥想思考以探究环宇之妙。文房不仅是文人训练和展示文人技艺的场所,更是延伸文人精神的空间。
笔、墨、纸、砚,雅称“文房四宝”或“文房四士”。前者源于梅尧臣《再和歙州纸砚》诗:“文房四宝出二郡,迩来赏爱君与予。”后者出自陆游《笔砚纸墨戏作》诗:“水复山重客到稀,文房四士独相依。”由于文人雅士珍爱文房四宝,所以给它们送了许多雅号。
文房用具除四宝以外,还有笔筒、笔架、墨床、墨盒、臂搁、笔洗、书镇、水丞、水勺、砚滴、砚匣、印泥、印盒、裁刀、图章、卷筒等等。在用于书法、绘画的文化艺术工具中,仅四宝,就已备受文人的喜爱和珍藏。
砚虽然在笔墨纸砚的排次中位居殿军,但从某一方面来说,却居领衔地位,所谓四宝砚为首,这是由于它质地坚实、能传百代的缘故。所以,现今社会上四宝中以砚最为多见,受人喜爱的范围也最为广泛。
现如今,还没有具体考证出砚台出现的时间,也只是经过考古发掘发现大致推断砚台是由原始社会的研磨器演变而来。秦汉之前的研磨器虽然具有砚台的一些功能,但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砚台。一直到秦汉之时,随着纸和人工制墨的发明,砚台也才被运用于研磨之中。到了汉代,制砚的工艺水平明显提高,而砚石真正走向全盛还是在唐宋,唐代国力强盛,诗歌、书法、绘画等文学和艺术空前繁荣,更是出现了许多著名的文人墨客。作为书画必需品的砚台也得到了长足进步。也正是在这时划分出了四大名砚:广东肇庆的端砚、安徽歙县的歙砚、甘肃洮州的洮河砚、山西绛县的澄泥砚。
东汉三足兽纹石砚
东汉卧虎盖三足石砚
汉代金边板砚
宋代海棠池花瓶式琴砚
北宋罗纹修长高足抄手歙砚
宋代荷叶池歙砚
唐代澄泥凤形砚
唐代澄泥砚
元代的砚形制表现为体形硕大,略显粗犷。简洁流畅,更加简约和纯正,明代的文人更是喜欢在砚台上雕刻诗句、铭文。因为这种风气,砚台逐渐脱离实用,进一步走向艺术品。明代的砚台由此也有了实用砚和观赏砚之分。到了清朝的康乾盛世时期,制砚业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各种材质、各种形制的砚台百花齐放。砚台的雕琢也更加精巧、繁复。清代是砚台真正完成了从书写工具到艺术品的华丽转身。
明代蝉形澄泥砚
明代荷叶形澄泥砚
明代鸠献蟠桃端砚
明代鱼化龙歙砚
清代澄泥凤形砚
清代端石荷叶砚
清代端石琴形砚
清代端溪老坑水岩松月纹砚
清代绿端琴形砚
清代歙石荷叶形砚
清代鱼化龙歙砚
自古以来爱砚之文人数不胜数: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爱砚爱石如命,曾见到巨石躬身下拜,称之为兄,更是提出了奇石收藏的“瘦皱透漏”的“相石四法”。对于砚台,米芾不光收藏,更是加以研究。一次,宋徽宗让米芾写字,米芾写完后大胆向皇帝索要砚台,说砚台他用了,皇帝不该再用。皇帝应允后,米芾抱着砚台揣进怀里,弄得一身墨汁也无所谓。这个故事的真假自然难以考证,但“米颠”的雅号更加活灵活现。米芾对各种砚台的产地、色泽、细润、工艺都作了论述,并著有《砚史》一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
近代爱砚之人,可推举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与其堂弟徐世章。徐氏兄弟都喜欢收藏砚台,哥哥起步早,新旧砚台都收,弟弟则后来居上,每以昂值索古砚。哥哥收到砚台总爱题刻一番,而弟弟则绝少题刻,尽量保持砚台原样。徐世章后来将所藏古物悉数捐献天津博物馆,由此让天津博物馆成了收藏砚台的著名博物馆。徐世章平时生活节俭,可是藏砚的时候不惜重金,只要让他盯上了,多贵都买,有的砚台甚至可以换一个大宅院,这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来说,都是难以想象的。每当收藏到好砚台,徐世章都会把砚台送到北京琉璃厂,请高手制作红木砚盒,并考证其传承出处附于砚盒之内,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
他在《藏砚手记》中写道:“吾人收集古人之砚,不独以砚材之极美,刻工之精细,而在充分表现其人之心灵、意境、节操、哲理、情绪、诗意等,形之于砚。”
明代高濂所著《遵生八笺》中说:“砚为文房最要之具。”自古以来,文人士大夫将精神追求寄托于文房之中,北宋诗人苏舜钦也认为“笔砚精良,人生一乐”,可见文房之乐乐无穷也。
秋爷
「之道」「之器」「是色」